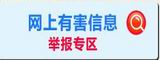回想农村下到户的第八年,山村人家夜里的点点灯火盘算成了满天的星斗,一声狗叫在这山唱响,那山久久地回应,连成一片欢叫。家家户户都在作修新房的筹备。而盛家碥一家单僻户在大石包的落塘里,被恣势的野树掩隐得只剩一块轮廓。原来四合院一大家同姓人都搬迁到大路旁,撇下盛月星孤单单的一人。左邻右舍的拆除,使排立房梁东拉西扯,歪斜欲倾,只剩下他孤零零的几间坯房,他索性拆了便卖,保留一间住房。因为没钱他不牵电灯,依然点着煤油灯,一盏孤灯总是在低矮处晃荡,幽深而让人耽心。这些年我在外地打工,已有好儿年没有见过他了,远看他的黑屋古墓似的冥寂。
盛月星是我的长辈,是我的忘年交,也是我诗文的启蒙人。因为本社一位老爷故世,我才从外地赶回来参加葬礼,顺便去看看月星爸。
一早,太阳已爬上白平观的松梢,我走过大方田来到他家,他正在菩提果树下逮懒虫子(蝉)。他看见我,把手里的懒虫子捏得吱吱响,说道:“懒虫子,叽叽叽,没的婆娘好伤心”。
我打断他的话头,递支烟给他,他双手接着,脸上的笑一直浮着,象不落的太阳。走进他屋里,一股酸叽叽的馊臭和尿骚味烩在一起,一种特有的寡公子味道。屋里除一副碗筷,锅铲瓢盆,房梁上吊下的编织袋大概是他的口粮。半截已经空了,被绳索勒的蔫瘪而垂头丧气。屋里的家俱一无所有,他说都送人了,他向来看薄钱财。常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村里人都劝他,凭他的头脑自身的力气,完全活的很好。可他我行我素,不进油盐,不听劝告。还鄙视他人的见识: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曰之: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村人都说:月星已成迂夫子了,拒人千里。社长说他,他以君子自居反唇相讥:
“噫吁嚱,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你枉自读过书?君子敬而无佚,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小人以智力争命故其心多怨。”
听了他的话,我知道他已中孔孟之道的毒,以圣人自居,以自身的清教来阐述古人的言论,以此安身立命,生活在虚幻清高的境界。他的土地承包给别人,每年只收取二百斤黄谷,不知他是怎样生活的。
我望着他壁头上写的诗词,已被油烟熏没。月星很有文才,读书的时侯,常常拿诗词请教他,远比老师还精通,让我五体投地。我把话题转到文章上来,想知道他这些年又写了什么好诗文,他两手一摆:
“天大的事情精微起,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的文章不用笔记,腹有经纶气自华,我有的是肚才,想听诗词?我念一首《怜书郎》给你听:
梦艺八耶,言屡耳闻。舀无水,炊无柴,食有禁,居无宁,文规思内无书纸,无砚无墨桌台遗;
文无思,字无凿,处处瑕庇漏于此,不知移居恩将戴,嫦娥寒宫处悠云。
怜书郎,苦嗖里,一淡伤心咽清泪,圪坤大,程如锦,匿专潜凿化虹霁…”
他闭目吟诵,超然物外,不知要念到牛年马月,我打断他的话:“星爸,你光这样读书也要吃饭,云松哥还去捡破烂卖钱寻食,你这样咋整?”
“好汉不吃嗟来之食,志士不饮盗泉之水,牛吃稻草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的福,我岂给侪辈相提并论,差也!”他有些忿忿生气,我忙给他敬上烟,他的笑挂上脸,开始滔滔不绝,如读天书,如念梵文。话毕,一时落寞。他似魂不附体已云游他乡不再理我。我留了一包烟,便告辞了。
从他家里走出来,正遇上云松哥摘了月星的南瓜要跑,见了是我,嘿嘿两声,真是饿鬼偷了穷鬼,君子偏遇到小人。
盛月星的父亲解放前是新津旧县机场的一个财务科长。解放前夕,本可以随军到台湾的,他追随刘文辉成了起义义士。解放后在老家的一个村小教书,细粮关成了饿死鬼。以后的各种运动他和他母亲成了“运动员”。包产到户后,他己四十出头,整日读孔孟,《论语》《中庸》,不关缄事。母亲一气之下病故。
面对月星爸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使被新思想所感,也不能撼动骨子里的迂腐,他可以引经据典来佐证他的观念。后来月星投靠了他远嫁在外地的姐姐,今不知何故又回来了,住进了保胜场敬老院。一晃已三十多年不见他了。
我专程回到保胜敬老院看他。到了敬老院,门卫通报有人找他,他走出来问:“哪个?”见是我,愣了一刻,喜出望外,迂腐中带点呆的笑回到他七十多岁的脸上,岁月已磨平了他的锐志,如一节枯木。
经得院长的同意,我带他到街上走了一圈,我们边走边聊,大致知道他的景况:他大姐己故,侄女远嫁,已无栖身之所,回老家没了土地。他说自已只有客死异乡了。
“没想到我仅给政府写了封信,村上就派人把我接回来,还安排我住在敬老院,有吃有住,有穿,每个月还有几十元零用钱。真是托这个好社会的福。现在我很安心。”
我请他进馆子,他不肯,说院里有纪律,不在外吃他人的东西。我塞给他钱,他也不要,说:我啥子都有,用不着钱。我只好买了袋水果,送他回敬老院。院里的老人们正准备吃午饭,他便把水果分发给他们。见他和大家融洽,相信他不再孤独。院长叫我一起吃个饭,我谢过。
月星爸把我送到门口,一再道谢我来看他。我也为他在这里安度余生而庆幸,为他年老融入到社会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