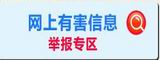点检春风欢计,惟有诗情宛转,余事尽疏残。彩笔题桐叶,佳句问平安。
——《水调歌头·解衣同一笑》
启点
在眉山,有这样一个小镇,唤为多悦。我来到这里,已经大半年有余。在此之前,尽管工作了些许年头,但我一直都固执地认为,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合格的基层工作者,只因我始终贪念于对过往的记忆,并且习惯感知于熟悉的环境,所以换做从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最终会选择背井离乡,来到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小镇里生活、工作。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因缘,带我来到了这里吧。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时节,驮着一包包的行李,独自悠悠地开着车。在穿过狭长而寒冷的隧道,驶过一眼望不到头的高速公路,不多久,大片的绿色植被,巍峨的大山,把彼时的道路拉得老长老长,被一点点抛在了身后,明晃晃的太阳打在车窗上,让人的眼睛,也不自觉地眯成了一条缝,耳畔,不时传来音响里干涩的乐声——
“红尘啊滚滚 痴痴啊情深 聚散终有时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随着面前从未见过的景色不停变化,仿佛间,自己像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空旅行。一直到抵达目的地,拨通手中最为熟悉的电话号码,向远方的爱人及父母报了平安之后,他们的嘱托才将我从恍惚变得清醒——平安就好,注意安全。
大半年过去后,现在回想起彼时彼刻,我才敢确定,那的确就是一段关于时间的旅行。自参加工作以来,因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总会收获不一样的经历。还记得大学才毕业时,在陌生人一声声的“骗子”的嘈杂声中分发广告传单,赚取了所谓的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来去了草原,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与牧民们打了大半年的交道;在人生第一份工作面前也曾“勇敢”辞职,一心要去大城市体验都市的生活,每天重复着方程式的节奏;在此之后,妥协于繁忙而拮据的生活,选择了公考,在2018年,我如愿成为了一名干部,也成为了一名驻村工作队队员……
落叶飘落在大地上,没有方向,更没有坐标,人亦是如此,我们都被命运所推动,最终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远方。我深知自己,对青春的不舍,但我亦深知,哪怕万般留念,想要不负未来,唯有朝过去挥手告别,而那些晦涩而阴郁的情感,也注定会如同被抛在身后的风景一般,消散不见。
长河
多悦镇,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我的栖息之所。这座小镇拥有四川盆地乡村的典型的浓郁生活气息,长着青草的路檐,紧凑而朴实的民房,夜里会有忙碌了一天的男人们三三两两聚在烧烤摊上摆着龙门阵,而平日寂静的场镇每隔几天便会因为十里八村的人们“赶场”而热闹……日子一久,农村的生活在恍惚间便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距离钢筋铁骨的都市生活,其实渺小的我们,或许还很远很远。
只不过,这些于我而言,其实也并无多大差别。如果,硬要说在大半年里,这里于我而言,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我想,大概便是往日在藏区所感受的那股苍茫,慢慢被平凡而磅礴的水汽所替代,灵魂也变得温润了起来。
但是这份温润起初却并没能我的内心带来任何一丝宁静和安详。每当想起远在他乡的家人,和过去的光景,内心的千头万绪,便涌上心头,犹如困兽。那是一种复杂而统一的对立情感,不停拉扯,相互纠缠,最终拉扯出两个自我,一个在田间野地里独自寂静,一个在灯火辉煌处黯然惆怅。
子来多悦豫,王事宁怠遑。三旬无愆期,百雉郁相望。
而在这个虚妄情感尚未平息的沉闷热夏,我也去见了多年未见的一些老友。我们因不同的理由来到了同样的土地,而在很多个夜晚,我们也会因枯燥而聚在一起,因饥饿而一同进食,就像一群居住在深山丛林中的动物一样,满足于对彼此的声声宽慰,满足于对食物的细碎咀嚼。“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再一起聊点什么吧……”抱着这样类似而细小的念头昏昏欲睡,日子,仿佛也开始变得简单而又充满期待。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物质始终大于精神,生活也始终大于妄想,感同身受的认知情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久而久之,忙忙碌碌的大部分的我们,活成了冷暖自知的状态,再也没有多余的情感或事物,能耗费我们无数不多的时光。或许,也正因如此,我始终坚定地认为,相比一个人对于生活的自怨自艾,我们更需要的,其实是对他人情感的无限贪婪。
人事聚散,岁月迢迢。时间,不可追,不可寻,明天无法揣测,当下瞬息万变,但它却是最好的见证,与人安慰,与人期待,平平安安,其实便已足以。
因为人世间何处归途,何处天涯,谁又说得清楚呢。或许远方亦是归途;或许故乡亦是天涯。心若荒凉,日日皆是凄苦飘零;心若安恬,其实处处皆是牧歌田园。
流沙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1927年初,22岁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已经完全瘫痪,即便病痛折磨,他却依然坚持以创作代替心中的革命,可惜,最初的手稿,早在邮寄的来回途中遗憾丢失。而直到1933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才真正得以完成。这本书,曾经陪伴了我无数个寂寥的夜晚。
孩提时候,其实是看不懂这书的。随后,当我自认能读懂这本书的时候,我早已与如今的妻子相恋,我大概是,从那时候起,也遇见了自己生命中的“达雅”。
那个时候,她还不是一个妻子,也还不是一个母亲。我们相隔千里,唯有一次次地通话,一次次地视频,去支撑着对彼此单薄的爱情。我们会聊彼此看过的电影,彼此看过的书,彼此看过的风景……
——“那么,丽达也好,达雅也罢,究竟谁对保尔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想,或许都不重要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我说不上来。我无法去深究萦绕在脑海里那些奇特的问题。正如眨眼间,我心中的孩童尚未长大,而我现实中的孩子却已蹒跚学步,即将步入学堂。家人的日常开支更需要我去维系,父母日渐老迈的身体更需要我去牵挂,而上级交付的工作任务远远比自己的只言片语更为重要。
“不要出任何意外”。成为了每一个平凡的我们,毕生的最终追求。
彼岸
上个月,记得还是休假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在即将返岗的那个夜里,嗅着妻子和女儿的鼻息,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尽是望不见头的人海,我牵着妻子的手,抱着孩子在人群里徘徊穿梭,最终在一个旋转木马面前停下了脚步。那是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巨大的旋转木马,我倚靠在栏杆外,望着妻子将女儿搂在怀里,坐在木马上放声大笑着,耳畔萦绕着的音乐,和她们的笑声融在一起。自己竟也不自觉地笑出声,醒了过来。
而第二天的天空,放晴得很早,阳光温暖的程度恰到好处,像是孩童的手一般,轻轻抚摸着我的鼻尖。匆匆喝过几口妻子熬的白粥后,我便踏上了返岗的路。临走时,她反复叮嘱我,记得要按时吃早餐,天冷了,一定要添加衣物,还有就是不要总抱怨工作,要好好上班。
那一瞬间,我是多么想和她分享昨夜那美妙的梦呀。但始终又怕孩子醒来,只得匆忙启程赶路。
那一天驶过盘旋的高速公路,看上去像是一条蜿蜒的河。哦,对了,就像曾经从事河长制工作时,经常巡护的那条河,即使肉眼看不见,每年河道的走向总会有些许变化,河床的高低也会随着汛期的更替而有所升降,而无数的砂石盘踞河谷,堆积在一起,像是一座座沉默的雕像,守护着荡漾的河流,守护着两岸的植被,守护着沿河的万家灯火,也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平安。
而相比于对虚妄事物的情感追求,我想,这种凝聚在一起的沉默力量,其实才是推动时间和故事不停向前发展的唯一理由。平安度过此生必经的修行,也为他人悲苦喜乐的蜿蜒大河,筑起足够支撑的坚实谷底——
我想,石头们,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吧。
(赵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