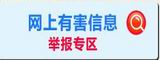岷江在彭山脚下拐了个弯,水波便裹着岸边的芦苇荡轻轻摇晃。我站在北街社区服务中心二楼的窗前,看楼下穿蓝马甲的网格员李大姐正牵着个垂头的小男孩往心理咨询室走。男孩的鞋带松了,她蹲下身替他系好,手指翻飞如白蝶。这一幕让我想起老家屋檐下年年归巢的燕子,衔泥哺雏时也是这般细碎又执着。
“这孩子叫小海,爹妈在东莞打工,去年奶奶走了,成天缩在教室角落里撕作业本。”李大姐把温热的红糖水推到我面前,杯底沉着几粒枸杞,像暗红的星子。社区心理咨询室的窗帘是嫩黄色的,墙上挂着孩子们画的“心情树”,有的枝桠缀满笑脸太阳,有的却爬满黑色毛虫。小海蜷在沙盘前堆城堡,突然抓起只恐龙模型狠狠砸向城墙,塑料碎片溅到我的手背,生疼。
二楼拐角传来手风琴声,是退休教师王老师在给情绪障碍的孩子们上音乐课。他总说:“琴键一响,心里堵的石头就能震出缝儿。”上周我去旁听,有个自闭症女孩忽然跟着《茉莉花》的调子哼起来,声音细若游丝,却惊得窗台上的绿萝都颤了颤。王老师布满老年斑的手没有停,琴声像春蚕吐丝,把那个瞬间织成了金箔。
深秋的清晨,我在彭山区精神卫生中心遇见张医生。她白大褂口袋里总装着话梅糖,查房时遇见攥着衣角发抖的患者,就悄悄塞一颗过去。有个患抑郁症的高三女孩曾把药片藏在舌根下,被张医生发现时哭喊着:“治好了又怎样?我爸还说考不上985就去死!”那天张医生陪她在医院后院的香樟树下坐到日影西斜,叶片缝隙漏下的光斑在女孩手背跳跃,像一簇簇不肯熄灭的火苗。
最难忘那场在彭山三中举办的校园心理剧。舞台上的男孩反串《丑小鸭》里的妈妈,当他把纸箱做的“蛋壳”撕开时,台下突然站起个满脸通红的学生:“我……我妈妈也是清洁工!”全场静了一瞬,继而爆发的掌声惊飞了槐树上的麻雀。后来听说那孩子考进了川师大的心理学系,朋友圈封面仍是那晚的星空。
冬至那天,我跟着调解员老周去处理家庭纠纷城。中村的出租屋里,十五岁的少女把美工刀抵在腕间,父母还在为弟弟的补习班费用争吵。老周不急不躁地煮起醪糟汤圆,氤氲热气中,少女突然抽泣:“周叔,去年生日您送我的捕梦网,我挂在床头天天擦……”瓷勺碰着碗沿的叮当声里,老周把调解书折成纸飞机,轻轻掠过女孩的发梢。
暮色漫过江面时,我常去平安桥头的24小时心理热线值班室。接线员小杨的记事本上画满月亮,有的圆润如银币,有的残缺似指环。前夜有个外卖小哥打电话,说送完最后一单听见《生日快乐歌》从别人家飘出来,突然就蹬不动车了。“杨老师,我女儿明早手术……”小杨把免提打开,我们对着话筒齐声唱完那首歌,电流声里传来压抑的呜咽,像岷江夜航船的汽笛。
昨夜,我又路过北街社区。心理咨询室的灯还亮着,玻璃窗上贴满新剪的雪花。小海在教李大姐折纸船,说要等开春放进岷江,“奶奶变成星星前说,江水通着大海呢”。江风裹着远处广场舞的乐声拂过,那些载着秘密与期盼的小船,或许真能驶向黎明的微光里。

 四川法制网
四川法制网
 法治文化研究会
法治文化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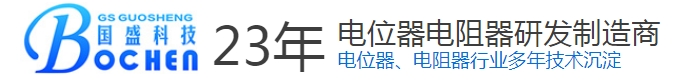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